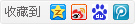"帮厨"主要是洗菜、洗碗,还有端茶敬酒女红类的事。
我们小屁孩就负责吃。
可以连吃三天。
结婚头一天是吃"猪甘花油",菜可以差一些,会上一二份罗卜。晚上安排二个童子男暖新床。
第二天一大早,一部份"动运"随同新郎和媒人去接新娘,搬嫁妆。准备在新娘家门口坐冷板凳。
谈好"开门"的钱后,"动运"可在新娘家吃一顿上轿饭,然后接新娘出发。一路上要安排人放炮仗。
进新郎家时新娘子不能踩到地,地上铺上麻袋一只一只交替前行。那时红地毯估计也没得买。
接下去拜完堂进新房再见长辈端茶收见面礼。
中饭是正餐,菜最好。
晚餐可以随便一点。晚饭后是"贺郎",仪式感很重的一项活动,主持人也叫"贺郎头"坐上位,新郎新娘坐下位,长条桌两边未婚男女坐得齐齐满满,桌上摆满瓜果糕点。
"日出东方一点红,红红腊烛摆当中!
"今天晚上xx结婚。。。。"
"贺郎头"不是谁都做得的,是专业的活,有固定的套话程序,要会唱会说会**绪,让整个活动热热闹闹欢欢喜喜恩恩爱爱。
长条桌两边所有吃喜酒的人,包括客人和全村人都在边上看热闹呢!
村里没有通电灯,用一种汽油灯,那是结婚专用的灯,会发出"嗞嗞"的声响,吉白色的灯光把屋子照得呈亮呈亮。
桌上坐的人都得表演节目,不会的学两声狗叫也行。
新郎新娘的节目是主线,怎么难怎幺弄,怎么黄怎么搞,除了不能表演现场直播床体节目,其他都可以。如果认为,所有喝酒人有份,第二天酒桌上兑现。
所以"贺郎头"出题很重要,决定战绩。
"贺郎"结束闹新房,有人提前钻在新床下听床,有人窗外听音,也有人把新房房门卸下拿床上物品"烤竹杠",都合规。
所以东家新房的门要做得牢靠。
第二天中午是请客,非亲非故的村乡干部和邻近德高望重的"乡贤"叫上一桌撑面子,贺新婚。
晚上吃"篾洛餐",三天来吃剩的菜到在一起烧上来,里面什么东西都有,味道酸酸的,挺好吃。
我们小屁孩,可以吃三天,吵三天,闹三天,玩三天,开心。
一般情况下,都会向老师请假,“喝喜酒"比啥都重要,老师也懂的。
那是乡里最大最大的事。
它承载了乡村文化民俗的骨架和精髓!
《乡旅拾趣》番外(十八)
村里人日不闭户,没有一户人家的大门上锁的。白天如果大人下地,小孩上学或者外出,大门都是洞开的,只把小掩门拉上。
那种半身高的小掩门可以防止家禽或者毒蛇等光顾家里。
从来没有听说哪一户人家丢失过东西。
对偷鸡摸狗的事是要被严厉惩罚的,骨子里都疾恶如仇。
村前的小水库曾经养过鱼,买了一些草鱼和鲤鱼的苗放养在水库里。
专门安排人员定时喂饲,看着浮在水面的鱼儿慢慢变大。
有一天晚上,村子南面山坡后面烟墩下村的一个小伙子溜到村里,拉起水库的起闭机(闸),放水偷鱼。
因为是夏天,有人赶潮"推七"(我在作品中介绍过那种海边推鱼虾的方式)回来,听到"哗哗"的放水声,抓了个正着。
也有可能还有同伙逃逸了。
全村人都被喊起来,聚在大樟树下。
那个人被绑在大樟树上,只穿一条短裤。
"这水库的水是我们的命,你要我们命!"
"把他扔水库里去!
有人上去打他巴掌,下手很重,嘴角流出了血。
我看着有点不忍和担心:"他会不会被打死?"
"别打了,要出人命的。"
说这话的是我叫四叔的友法的老婆,小婶婶是烟墩下嫁过来的。
"就要打死他!“群情激奋。
"有错好好说,不能这样打!"
我母亲过来了。"姑姑,救救我!"
我母亲的姐姐嫁到烟墩下,生小孩时死了。那里人碰到母亲大都叫姑姑姨娘。
"放了他!"
没人放人,也没人再打他。
母亲说话在村里是有份量的!
她小时候同桌吃饭长大的四位同房堂弟,个个人高马壮、撑门立户。
没有人敢不给她面子。
四叔友法解了绑在他身上的绳子。
母亲狠狠的骂了他一顿。
我看着他在黑夜中离去。
好象伤得不轻。
《乡旅拾趣》番外(…)
老家小沙是作家三毛的故乡。
很多人只知道三毛出生于重庆,少年时期生活在南京和上海,以后随父母迁居台湾,最后喜欢旅行的她写下了“万水干山走遍”等家喻户晓的作品。
但少有人知道三毛的爷爷是一个从老家小沙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。
最早读《雨季不再来》等作品时还不知道三毛的父辈是我的同乡,读了一本疯狂地找另一部,真有点象饥饿时找快餐店那般的急。
知悉她回乡省亲祭祖并落下些许故事,便兴冲冲去她故居拜访,原来就在我高中毋校的边上村落。
这个村叫陈家村,是一个陈姓聚居地,所以三毛原名叫陈平。
陈家村现在属小沙街道庙桥社区,和我出生的小山村同属一个社区。
三毛的爷爷少年外出打工,历尽艰辛,
手机阅读:http://m.77kshu.cc/218829/
发表书评:http://www.77kshu.cc/book/218829.html
为了方便下次阅读,你可以在顶部"加入书签"记录本次(第四十章 番外一2)的阅读记录,下次打开书架即可看到!请向你的朋友(QQ、博客、微信等方式)推荐本书,禾火江水谢谢您的支持!!